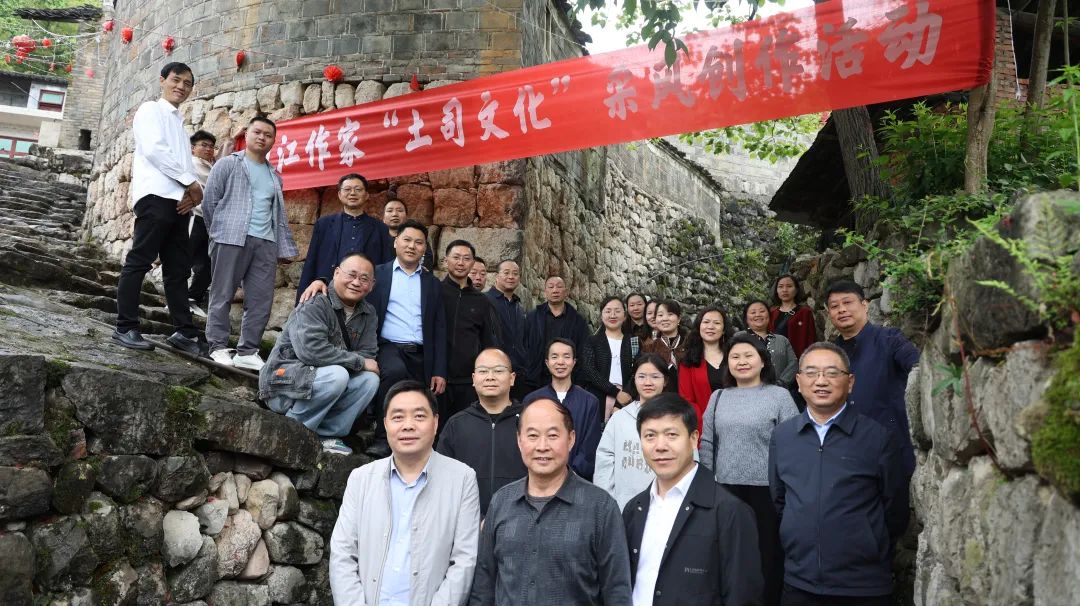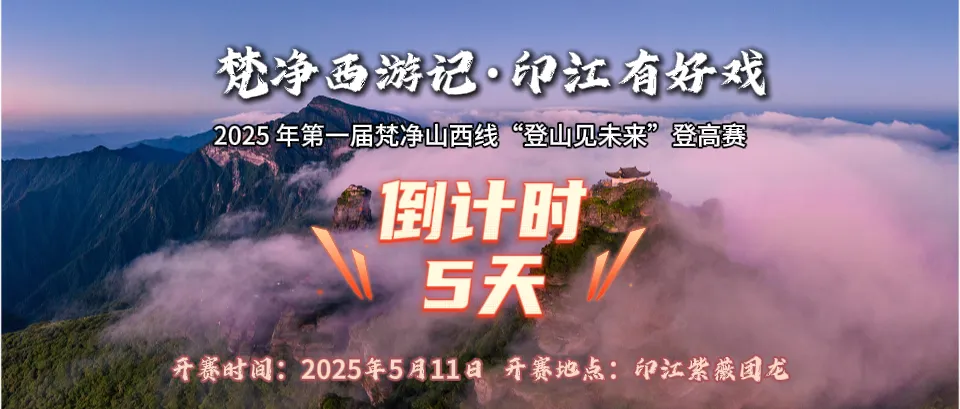
四月的朗溪,被铺天盖地的嫩绿所笼罩。黄红相间的樱桃儿与洁白的柑柚花儿星星点点地缀于其间,清幽馥郁的香气扑鼻而来,令人沉醉。多情的天气以细雨和雾气为笔,将朗溪绘成一幅淡墨长卷,让穿梭于丛林间的青石路泛着温润的光泽,仿佛每一块石板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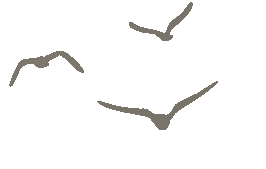
杨秀强老先生站在甘川琢玉山庄门前,胸前的紫袍玉带石小坠件随动作晃动。他笑着向采风组招手:“听说你们要来,我特意从铜仁赶回来!前些天,省里专家在这儿发现了殷商时期的陶瓷片……” 作为文化旅游局退休的老局长,也是深耕印江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,他精神矍铄,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
琢玉山庄由杨老开办,这里不仅是休闲娱乐的饭庄,还设有紫袍玉带石加工场地,更有书屋陈列着文房四宝和众多藏书,文化氛围浓厚。“琢玉” 二字,既寓意着对紫袍玉带石的精心雕琢,也暗含着对文化精髓的探寻。书屋内,一张大书桌旁,毛笔和砚墨尚带着湿润,仿佛刚刚有人在此挥毫疾书。众人围着杨秀强,看着他从书架上取出《幽兰杂记》《匹夫论丛》《印江苗族文化综述》等书籍,随着他的讲解,土司的历史如画卷般在眼前展开,众人听得入神。

明洪武元年,朝廷派遣沱江宣抚使田儒铭从湘西率土兵开赴黔东“平蛮”,他也因此成为朗溪田氏的始祖。
田儒铭,字尚贤,号靖轩(1318 - 1401)。元至正年间,他征讨十五洞有功,被封为昭信校尉定蛮威武大将军敦武侯。洪武元年,奉调助剿周文贵于鄱阳湖,凯旋后,招抚中林验硐、筸子坪、五寨、朗溪等地蛮夷,打通云贵大道,被诰封忠顺大夫,任沱江宣抚使。他的五个儿子随征皆有功,所开辟的地方被赐分守。洪武五年,五子被敕封世爵,各降印信承袭。
洪武十三年,四川酉阳司冉万花策反朗水十五峒的苗头,田儒铭率五子再次出征平定。此后,长子茂文为五寨长官司,次子茂武为筸子坪长官司,三子茂弼为平头长官司,四子茂良为中林验硐长官司,五子茂能为朗溪长官司,朗溪田氏土司制度初步建立。
从明代田茂能至田养民的约三百年间,是朗溪土司制度发展、巩固与强盛的时期。清顺治十五年,朗溪等长官司随府投诚,设司仍旧。清康熙九年,因苗民侵边,朗溪土司衙门迁住木桷寨,副土司衙门迁住木社寨。直至清末宣统二年,最后一任长官田儒煓为止,朗溪土司制度穿越千年,田氏土司走过了五百四十多年的历史。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,不仅是田氏家族的奋斗史,更是朗溪地区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篇章。

蒲氏,被朗溪田氏尊为始祖婆,其墓位于朗溪镇孟关村,为印江县文物保护单位。
跟随杨老的脚步,穿过朗溪街,沿着孟关村主路边的小路步行几十米,便来到蒲氏墓前。一座小山之上,石头堆砌的小径蜿蜒而上,山腰处立着石碑,记载着墓主的身份和保护信息。墓为浑圆的土堆,体积庞大,上面插满“亲杆”(用于挂祭祀纸饰的树杆),挂满 “亲纸”(挂在坟头表示祭祀和悼念的纸饰),土香炉里残香残烛堆积,彰显着子孙的兴旺和后人的景仰。山上松柏摇曳,仿佛在诉说着墓主人的传奇。

朗溪老街,青苔斑驳的小巷里,每一处痕迹都是岁月的符号。杨秀强停在一堵断墙前,墙基嵌着的半块雕花条石,“二龙戏珠” 的纹样清晰可见,这是乾隆年间田氏宗祠的遗物,见证了汉地石匠与苗疆雕师的合作。他的鞋底碾过墙根的碎瓷片,那是明代的青花残片,仿佛让人看到当年朗溪码头众帆竞发,物产集散的繁荣景象。

土司衙门遗址,现代办公楼与残垣断壁并存。杨秀强蹲在刻有“田氏宗祠” 的柱础旁,指尖划过风化的铭文,描述着 1974 年大火后的遗迹。镇政府门前的石阶、墙角的雕花,皆是当年旧物,历史就藏在这些细节之中。


回龙寺的大雄宝殿在回龙堡顶若隐若现,门联“龙游朗水浪转波回结成圣” 字形苍劲有力。杨秀强穿过松林,指着山脚下的溶洞,这里古称 “四十八堡龙头地”,溶洞中的钟乳石形似观音,故名 “观音岩”。《朗溪长官司志》记载,田儒铭征剿后,在宗祠祀关帝、在寺中塑观音,体现了儒释并祀的治民文化策略。

从朗溪街前往荥家湾,山路弯弯绕绕,却在进入巴山溪(古称爬山溪)时,展现出大自然的绝美画卷。两山苍翠,崖壁如斧劈刀削,中间溪流潺潺,让采风的女同志欢呼不已。
抵达荥家湾时,天已放晴。陶罐厂的天井积着雨水,土窑历经岁月洗礼,静卧山坡。65 岁的刘祖明握着半块鱼纹陶坯,指尖摩挲着缠枝纹,那是照着老辈人传下来的土司酒坛刻制的,当年田氏宗祠摆宴,必用此窑烧制的 “九龙坛”。走进作坊,未上釉的陶坯静静陈列,手工捏塑的云雷纹,是苗族图腾与汉地吉祥纹的巧妙融合。刘老汉感慨,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让秘方险些失传,全靠口耳相传才得以延续。

王家巷子深处,高厢房的吊脚楼在雨中巍峨矗立,门额“积善家” 虽已褪色,却难掩当年气派。这是光绪年间举人王廷章的宅院,他既是土司幕僚,又主讲印江书院,家中陈设融合汉苗风格,正房的 “三槐堂” 匾额与厢房的苗族百褶裙纹木雕,是 “土流合治” 的缩影。
居洞沟营盘的石墙在云雾中显露峥嵘,枪眼遗址整齐排列。乾隆四十七年为固边防而建,石块间未用灰浆,全靠匠人精准测算,民国时土匪据守却不战而退,尽显营盘的森严气势。远处的烽火台遗址,曾是十五峒传递信号的制高点,一炷烽烟便能召集千军,是山地文明的智慧结晶。
大关桥的单孔石拱倒映在爬山溪中,桥额“大关桥成,四境丰享,千秋万古,永播芳名” 的刻字被雨水冲刷得棱角分明。雍正九年始建木桥,道光十年改石拱,碑文里的 “田君次山” 是末代土司后裔,桥栏上的卷草纹与土司衙门雕花如出一辙,见证官民共筑的岁月。
返程经过凤竹路摩崖,“凤竹路” 三个楷书大字清晰可见,下方小字记载着乾隆年间田君聘复修此路的善举,如今紫袍玉带石工艺复兴,老匠人们从驿道石材中汲取灵感,让古老技艺焕发生机。
此外,朗溪镇还有古驿道,三道牌坊遗址,多处土司墓群、古营盘等;木黄镇、新业乡、合水镇等地也留存着与朗溪土司相关的遗址和宗祠。万历年间,印江进士肖重望奏请设立县学,得到土司田兴邦支持,捐学田、送子求学,开启了朗溪子弟“读汉书、习汉礼” 的风气,是土司主动融入中华文明的关键一步。
现今,县文化部门收藏的土司物件及文献,如正副土司长官司印、官帽、《征蛮实录》《朗溪田氏族谱》等,为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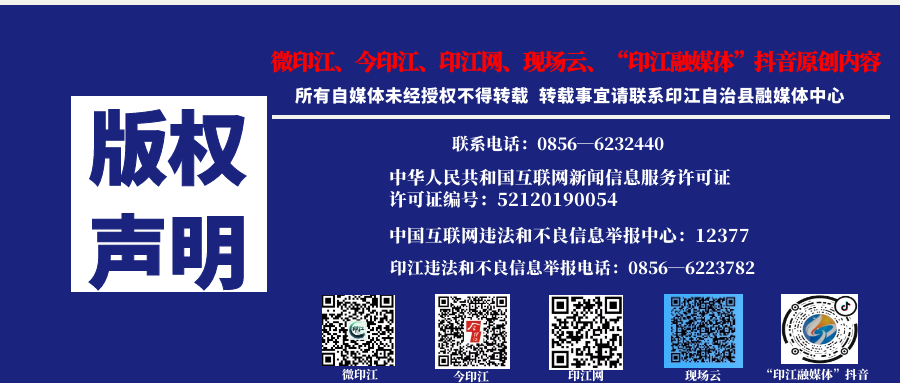 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编审:张江勇 编辑:阙莉淑
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编审:张江勇 编辑:阙莉淑